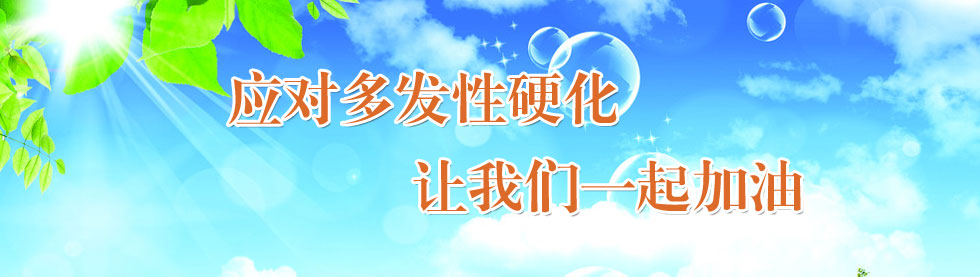
“神奇子弹”:抗菌药物改变的医疗史对人类而言,抗菌药物的产生就好比是获得了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细菌感染疾病的斗争。但是由此带来的“抗生素崇拜”,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值得警惕。或许,一个新的科学共识正在形成:只有认清人类同细菌的长期共生关系,我们才能找到人类健康的另一条途径。医院,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手拿青霉素与其他药物测试的标本。他在年发现了青霉素抗菌药物崇拜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相反,它基于现代医学的实践,“与细菌为敌”是现代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信条之一。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堪萨斯医生亚瑟·霍茨勒曾坦言:“我知道,某些疾病即使处于初期,我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我常常在接触马具之前就明白这次出诊毫无用处……”20世纪以前的漫长年代,结核、白喉、脑膜炎和产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困扰。传统医学没有战胜这些疾病的良方。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除此之外,能依靠的只有自然、运气、家庭和宗教。年,荷兰绸缎商人列文虎克(AntonivanLeeuwenhoek)被一本书迷倒了。英国博物学家、精于显微镜制造的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出版了一本《微小图集》(Micrographia),描绘了他在放大镜下看到的惊人世界:一只苍蝇眼睛的平面,一只趴在人头发上的虱子,一片软木的单个“细胞”。这本书令列文虎克以无尽的热情投入到了显微镜的研制中。他一生磨制了多个透镜,有一架简单的凸透镜,其放大率达到了倍。年,列文虎克惊讶的发现,人的口腔中居然躲藏着许多“小动物”:“这些小家伙几乎像小蛇一样用优美的弯曲姿势运动……在人的口腔牙垢中生活的动物,比整个荷兰王国的居民还要多。”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细菌时发出的感叹。后人从列文虎克写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上百封附有图画的信里断定,他第一个观察到球形、杆状和螺旋形的细菌,还第一次描绘了细菌的运动。英国著名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从列文虎克的发现中找到灵感,写出了一首著名的四行诗:博物学家告诉我们,跳蚤身上有小跳蚤叮咬;这些小跳蚤又被更小的跳蚤叮咬,如此这般,没完没了。荷兰人列文虎克第一个观察到球形、杆状和螺旋形的细菌,并第一次描绘了细菌的运动正如伽利略在17世纪早期用望远镜扩大了人类对天空和宇宙世界的认识那样,列文虎克用他的显微镜对准日常物质,展示了另一个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维度。然而,这些居住在人类身上的“小动物”与人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微小图集》出版的那年夏天,伦敦15%的人口(3.1万多人)死于黑死病。但在约两个世纪之后,人们才最终明白这些看似脆弱“小动物”能够置人于死地。攻克细菌年,德国医生科赫(RobertKoch)所在的沃尔斯顿地区出现了牛羊死于“狂怒病”的现象。醉心于研究的科赫用显微镜观测从病死牛羊身上抽取的血液。他发现,所有这些样本中都可以发现“小木棍”和“线条”形状的微生物,而它们绝不会出现在健康牲畜的血液里。科赫将这种疾病命名为“炭疽病”,并深信这些“小木棍”和“线条”是疾病的病原。在科赫以前,欧美的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已经产生了病菌理论的支持者。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用他著名的天鹅颈烧瓶證明了细菌并不会从无菌物质中自发产生,它们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不可见的空气里。巴斯德甚至也提出:“每一种疾病,都是由一种很小的、有生命的细菌引起的。”但是并没有人能够论证他们的观点。4年后,科赫终于寻找了一套方法。他用火焰消毒一块擦干净的薄木片,然后在小白鼠尾巴的根部切开一个小口,用木片蘸上一滴病死动物的黑色血液,涂抹在白鼠的伤口上,再把它单独关进一只笼子里,便于观察。接下来,他解剖病死的小白鼠,提取它的血液标本,不出所料,显微镜下的视野里再次出现了熟悉的“小木棍”和“线条”。科赫研究的第二步是将玻片加热灭菌,放上一滴用来培养细菌的牛眼分泌液,再将一只刚刚死去的白鼠的脾组织放在分泌液中,盖上磨有凹槽的载玻片,用凡士林将两块玻片密封起来。于是,他得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炭疽杆菌的分裂繁殖。最后,科赫将自己培育的炭疽杆菌接种到小白鼠的尾部。24小时后,小白鼠死了。这套今天看来并不复杂的实验使得人与细菌的关系产生了第一条重要的常识:细菌可以致病。当细菌和疾病挂钩之后,医学对于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有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明确对策。年,曾在科赫的细菌实验室工作过的德国病理学家埃利希,做了一个精确的比喻:现代药物需要一颗“神奇的子弹”,既可以摧毁细菌细胞,又不会伤害人体本身。这来自他的观察——细菌的细胞从根本上和人体的细胞有很大的区别。“神奇子弹”出现的前夜是现代医学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时光。在医学史上,令人唏嘘的两个“玛丽”的故事连接着黑暗和光明。“伤寒玛丽”是黑暗年代的最后注脚之一。她的命运生动展现了,人类找出了致病菌敌人却无计可施的困境。20世纪初,纽约的东下城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只有极简陋的排水系统,也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纽约每年有0名伤寒患者,他们将经历持续几周的痛苦的高烧、头痛、腹泻和精神狂乱,最后至少有10%的人无法熬过折磨。年夏天,银行家华伦带着全家去长岛消夏。8月底,华伦的一个女儿最先感染了伤寒。接着,华伦夫人、两个女佣、园丁和另一个女儿相继感染。有处理伤寒疫情经验的工程专家乔治·索柏将目标锁定在了已经消失的厨工、爱尔兰移民玛丽·梅伦身上。他从职业中介公司提供的材料中慢慢拼凑出10年来玛丽的生活片段。他吃惊地发现:“在过去10年里,她所工作的家庭都爆发了伤寒,而且,无一例外。”德国医生科赫。他证实了细菌和疾病的关系年3月,乔治·索柏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玛丽。这场相遇令他猝不及防。“我尽量使用外交语言,但玛丽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她抓起一把大杈子,朝我直戳过来。我飞快地跑过又长又窄的大厅,从铁门里逃了出去。”玛丽根本无法相信是她将伤寒传染给了别人。五名警察把医院,医院检验结果证实了索柏的怀疑。那个年代,“健康带菌者”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现在我们知道,没有生病的人或生病痊愈之后人身上也能找到病原体,他们本身不会生病,却可以把病传染给别人。在无法有效杀灭细菌的年代,公共卫生部门只能有一种选择:携带伤寒杆菌的玛丽被送入纽约北哥岛上的传染病房强制隔离。两年后,玛丽向卫生部门提起诉状,指控他们侵犯人权。年2月,当地卫生部门与玛丽达成和解,解除对她的隔离,条件是玛丽同意不再做厨师。然而年,医院暴发了伤寒病,25人被感染,2人死亡。卫医院的厨房里找到了已经改名为“布朗夫人”的玛丽。回到纽约北哥岛,医生对隔离中的玛丽使用了当时可以治疗伤寒病的所有药物,但伤寒杆菌仍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她的体内。玛丽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此后,她再未离医院,直到年去世。抗生素改变医疗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痢疾与伤寒比战争本身引起的死亡更多。和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蔓延,感染了5亿人,将近占世界总人口的1/4,死亡万~0万人,其中大多人死于细菌性肺炎引起的并发症。“当我在年9月28日早晨醒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因为发现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而将改变整个医疗。”亚历山大·弗莱明在那个被污染的培养基发现青霉菌的抑菌作用的故事大概是医学史上最令人熟知的桥段了。但事实上,这一发现距离“神奇子弹”的出现还有漫长的距离。年,在《不列颠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的研究论文时,弗莱明对青霉素能杀菌的叙述只有一小段。在后来的10年里,他发现青霉素对任何动物无害,通过研究不同酸碱度下青霉素的性质,搞清楚了怎样让这种药品变得更稳定,但他远没有能够完成最重要的一步:创造出临床能够使用的有效制剂。年,弗莱明已经放弃对青霉素的研究,而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对青霉素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英国牛医院(RadcliffeInfirmary)的病理学家弗洛里(HowardFlorey)和生物化学家钱恩(ErnstChain)沿着他的路走了下去。这一年,他们从青霉菌中分离和浓缩出了可以用于实验的青霉素,并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成功。但一个致命的瓶颈是,要提高青霉素的产量太难了。这一年的秋天,牛津的一位警官在修建花园里的玫瑰时划破了脸,感染扩散到了眼睛和头皮。医院,德国发明的磺胺类抗菌药品效果有限,很快感染蔓延到了肺部。弗洛里建议使用青霉素。五天的治疗后,警官的病情开始好转,但全部的青霉素已经用完了,病人最后死于无药可用。两年后,医院,一名31岁的女患者安妮·米勒(AnneMiller)已经因为败血症生命垂危,在科学家们的建议下,医院使用5克青霉素进行人体试验。在医生给米勒注射了青霉素后的第二天,她的病情就开始好转。此后,安妮·米勒健康地生活了60年。但那5克药剂已经是全美国所有的青霉素储量的一半。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人们对“神奇子弹”的渴望。政府、大学、公司和研究所纷纷投入到了这场与伤兵细菌感染较量的赛跑里。“伤寒玛丽”去世后的第四年,医学史上的“霉菌玛丽”出现了。弗洛里让手下的实验人员去水果摊发霉的烂水果里寻找高产的菌种。玛丽·亨特看上了一只哈密瓜——黄绿色的霉菌已经长到了深层。弗洛从这只瓜的绿毛上提炼取了黄绿霉菌,这株霉菌使青霉素提炼的产量提高了倍。后来,威斯康星大学和卡内基学院的研究人员用X光或紫外线照射它,使青霉素产量达到了过去的多倍。正如埃利希对“神奇子弹”的预期一样,青霉素之所以能够在不损害人体细胞的前提下杀灭细菌,是因为其有效成分青霉烷能使病菌细胞壁的合成发生障碍,导致病菌溶解死亡。今天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一般会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对细菌发起冲击:它们像青霉素以及它的衍生物所表现的那样,向细菌制造细胞壁所需要的部件进攻;或者它们能够抑制细菌合成蛋白质,而细菌需要蛋白质来执行包括消化食物、构筑细胞壁、运动、繁殖、抵御入侵者与竞争者在内的一切重要活动;再或者,它们会扰乱细菌分裂繁殖的能力,破坏它们的增殖过程。在细菌无法“扩军”的情况下,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将有机会清除它们。“二战”战场成为青霉素的临床试验场。年,美国生产了亿单位的青霉素,只能满足1万人次伤员使用。当时战时生产委员会主管青霉素生产的埃尔德(AlbertElder)给各个工厂写信:“你们要告诉每一个工人,今天每生产一支青霉素,几天后就能在战场上挽救一条生命,或者救治一个伤员。把这条标语贴到工厂里,印在工资的信封上……”年6月诺曼底登陆时,每一个英美联军的伤员都能够得到救治了。从年下半年开始,药物的供应已经足够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的盟军士兵。从战场凯旋的抗菌药物在临床治疗上也大放光彩。年,发表在《临床探索学报》(JournalofClinicalInvestigation)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青霉素治疗64名肺炎患者的惊人疗效。65年后,年,美国的医疗人员开出了2.58亿例抗菌药物,相当于每例处方当中就有个含有抗菌药物。对人类而言,抗菌药物的产生就好比是获得了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细菌感染疾病斗争的竞技场。结核、白喉、脑膜炎和产后败血症,那些人类历史上猖獗的细菌性感染疾病被迅速遏制。如果没有抗菌药物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想象外科手术在20世纪进一步突飞猛进。一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中国国家卫计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曾指出:“抗生素的使用将人们的寿命平均延长了24岁。”学会与细菌共生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发生流感。至年春季,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近0万人死亡。因为西班牙有万人感染,连国王也染上此病,故得名“西班牙流感”相比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干净得多的环境里。我们饮用消过毒的水、使用杀菌洗涤用品清洗我们的食物和身体,城市的环境衛生系统也以一尘不染的街道作为追求。感染性疾病在抗菌药物的抗击下不再令我们闻之色变,但很显然,我们的时代有自己的健康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科学顾问、纽约大学人类微生物组计划负责人马丁·布莱泽(MartinBlaser)在《消失的微生物》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迷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现代疾病几乎同时在发达国家里骤然增多,并蔓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你我都能感知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敏性疾病,你是否感到:你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患上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世界变态反应组织(WAO)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已达22%,我国发病率也已经超过了20%,平均五个人中就有一人过敏。根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殷勇教授的数据,在上海这个中国公共卫生和生活水平位居前列的城市,0~14岁儿童的哮喘患病率已上升到7.57%,超过20万人,几乎每10年翻一番,为全国之最。马丁·布莱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源于他早年对幽门螺杆菌产生的疑问。年,澳大利亚学者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并证明该细菌感染胃部会导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淋巴瘤甚至胃癌。5年,两位研究者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如今幽门螺杆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最高警示级别的I类致癌物,幽门螺杆菌感染使胃癌的患病危险增加了2.7~12倍。如果你在体检中查出胃中有幽门螺杆菌,医生多半会向你提出建议:使用主流的含有两种抗生素的三联疗法将它们从你的胃里清除。马丁·布莱泽并没有否定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的研究成果,令他好奇的是:为什么在他们之前,人们从未想过研究幽门螺杆菌与胃炎之间的关系?答案很可能是:过去的研究根本不会将这种细菌视为疑犯:遗传学研究显示,人类携带幽门螺杆菌已有十几万年,这个时间跨度是目前的检测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有理由认为,从20万年前智人刚刚出现在非洲大陆的时候,这种微生物就已经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9世纪的医生在几乎每个人胃里都发现了这种弯曲螺旋的细菌——你很难认为人人都有的细菌是病原体。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带菌者已经变成了少数派。而促成这变化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干净的现代生活。马丁·布莱泽接下来的研究发现则更为有趣:在我们清除胃里的幽门螺杆菌时,我们清除的不只是胃炎和胃癌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胃是一个彻底无菌的环境,因为我们的胃酸与汽车电池里的酸强度相当。但幽门螺杆菌如此特殊,它基本上只分布于我们的胃部。我们的消化道有一层厚厚的胶质黏液保护层,它就生活在胃部的这层黏液里。当胃的产酸细胞的成熟时,一些幽门螺杆菌便向这些细胞注入蛋白质,使酸度降低到幽门螺杆菌所能够忍受,但又足够杀死大多数其他微生物的程度。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一个没有幽门螺杆菌居住的胃势必比一个有幽门螺杆菌定居的胃分泌更多的胃酸。马丁·布莱泽认为,幽门螺杆菌的消失已经导致古老的平衡被打破了,它的后果绝不可能全是正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胃液反流造成的胃食管反流疾病,从年开始增长,现在是发达国家里增长最迅速的疾病之一。在美国为例,10%~20%的成年人都受其困扰。如果胃食管反流疾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它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疾病,如胃酸损伤人体组织并逐渐恶化成食管肺腺癌。在美国,食管肺腺癌曾经非常罕见,在美国所有的食管癌中仅占5%,目前却成了所有主要癌症类型中增长最为迅猛的一个。在过去的30年里,它增长了6倍,在美国所有食管癌中占的比例超过了80%,并且在发达国家里持续攀升。马丁·布莱泽的研究显示不携带螺杆菌的病人患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概率更大。有的研究成果显示了8倍的巨大差异。马丁·布莱泽对幽门螺杆菌的研究暗含了一个深刻的可能性:我们很可能需要回到我们体内的细菌身上去寻找困扰人类的现代疾病的根源。困扰人类的免疫系统疾病也同样如此。冯·穆蒂乌斯(ErikavonMutius)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过敏症专科医师冯·穆蒂乌斯开始对生活在大城市慕尼黑与生活在周边小乡镇的孩子的过敏症及哮喘的发病率进行比较,她发现乡下孩子的发病率明显更低。当时,许多人将哮喘和过敏症的原因归结为空气污染,但穆蒂乌斯的统计员却得出一个观察结论:“那些家里用煤和木头取暖的孩子似乎受到保护。”那个时候,冯·穆蒂乌斯根本不敢发表这样离经叛道的结论。几个月后,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冯·穆蒂乌斯立即意识到,她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让她得以比较同一种族却生活在极其不同环境下的人们的哮喘和过敏的流行率。当时,联邦德国在空气质量标准和废气排控方面的严格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民主德国则是受到严重污染的工业中心。接下来的两年里,冯·穆蒂乌斯和她的小组为东德、西德两个地区的多名儿童做了过敏和哮喘测试,并将结果与其病史及父母亲的调查问卷做比较,旨在找出过敏的证据,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她发现,民主德国儿童有较高的支气管炎发病率,这标志着气道损害,正像吸烟者受到的气道损害,这很可能是空气污染的结果。但同样是这些孩子,与西德的孩子相比,他们得花粉症的可能性只有后者的1/3,得哮喘的可能性也要低1/3。超过1/3的西德儿童被证实有过敏,而东德儿童则不足1/5。德国统一5年后,当穆蒂乌斯重回位于东德的莱比锡的时候,她发现,当地孩子花粉症的发病率增加了1倍,湿疹的发病率增长了50%。相应的观察是,德国统一后,东德家庭迅速采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在饮食上,进口的、加工食物代替了原来从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未经高温消毒的奶制品和没洗过、新鲜采摘的农产品。当然,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洁净了。能提供解释的可能还是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群系。它们组成了免疫系统的第三纵队。第一纵队是人类先天性免疫系统,包括保护着人体表皮及黏膜的细胞或分泌蛋白。它们可以“识别”大多数细菌共有的结构模式,从而消灭这些细菌。第二纵队是适应性免疫系统,它们依赖于特异性的抗体来识别病原体上高度特异的化学结构。而第三纵队就是微生物免疫,这些长期的住户可以以各种方式抵御外来者的入侵。进一步的,一些研究认为,多种自身免疫病在发达国家中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也可能与我们体内的住户有关。多种自身免疫病I型糖尿病、狼疮、多发性硬化、风湿性关节炎,它们都是由于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健康组织引起的。流行病学观察显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发病率相比,在那些人们亲近土地,喝未过滤的水,吃的食物几乎未经加工的地区,这些免疫机能紊乱病症很少见。一种推论是,人类大约年的文明和伴随而来的瘟疫,以极具侵略性的方式培育出了免疫系统,它是一种内在的、被大大小小的感染加强的攻击系统。公共卫生设施、抗生素和童年的疫苗大大减少了人一生中得疾病的炎症负荷,但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遗传情况却没有相应发生改变。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进入我们体内的细菌就开始帮助我们调试我们的免疫,帮助免疫的发育。我们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只有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区别“我”与“非我”。微生物正是“指导”这一过程的第一任老师,“教会”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危险。而在缺乏“老师”的情况下,免疫系统的学习也就出现了问题。在过往的研究中,抗菌药物化合物大多是从土壤中的细菌内进行采集的。现在,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住在我们身体里的细菌身上去寻找新的灵感。年7月,《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安德烈阿斯·佩舍尔(AndreasPeschel)所带领的团队完成了相关实验。研究小组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只存在于30%的人的鼻腔内,而70%的人的鼻腔内却没有。”研究显示,在那些不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人的鼻腔里,里昂葡萄球菌(S.lugdunensis)能够生成可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战斗”的抗生素。科学家将这种新型化合物命名为“Lugdunin”。在小鼠实验中,这种新发现的抗生素能够消灭或改善皮肤感染细菌,并且尚未發现有任何不良副作用。安德烈阿斯·佩舍尔说,人体菌落可以看作是新型抗生素的来源所在。或许,一个新的科学共识正在形成:只有认清人类同细菌的长期共生关系,我们才能找到人类健康的另一条途径。孩子生病,迷信还是拒绝抗生素?在儿科诊疗中,用不用抗生素、用何种抗生素,这首先应是一个医学判断。但当屡屡面对家长的催促、焦虑与指责时,医生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妥协?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下定的决心。现实情况往往是,在医生的判断和家长的态度之间寻求折中与妥协。“用不用抗生素”折射出的已不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掺杂了社会环境、医患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的权衡。家长对待抗生素的两个极端——拒绝或迷信夜晚,常常是儿科急诊最繁忙的时候。医院的儿科急诊大夫,王琨蒂最多的时候,曾一晚上接诊了位病人。到早上交班时,她整个人已经直不起身来,只能靠护士搀扶着拖下去。她笑问:“这地板昨晚打过蜡,你能看得出来吗?”医院的地面每隔几天就有专人打蜡,光亮得能映出人影,唯有儿科急诊室的地面,经过整晚的“碾压”,第二天早上就根本没法儿看了。“小孩来看病,一来至少有两个家长跟着,四五个家长也是常事。一晚上相当于有多个人从儿科急诊室的地面碾过去,这地板可不就不亮了。”“成年人的诊室几乎都是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两位大夫在一间诊室里看病。我们这儿看不了,太乱。”在王琨蒂的印象中,医院里最嘈杂的地方。“小于3岁的孩子抱进来几乎都在哭,不大声点和家长交流,根本听不见。”有时候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意见不一致,恨不得直接就在诊室里吵开了。“有婆婆数落儿媳妇的,有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呛起来的……”王琨蒂有些自嘲地苦笑道,“我们这儿总是特热闹。”儿科急诊室外,几乎每晚都排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大长队,可实际上能分配给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总是很有限。“坐在你面前的病人,总嫌你看得快,好不容易排到了,医生怎么几分钟就打发了?”事实上,按照人流量计算,平均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只能在3分钟到5分钟。“即便如此,排在后面的家长又总是催促‘你能不能快点啊!”这让王琨蒂也很无奈,“已经够快的了,不能再快了。”在敏感季节,来儿科急诊的病人大多是呼吸道感染问题。“从去年10月开始病人逐渐增多,到11月份人数一下子飙升上去,整个冬三月我们都忙得快飞起来了,连急诊带门诊带病房,几乎都是呼吸道的病人。”在王琨蒂的印象中,得病的大部分都是五六岁以下的孩子。“冬季病毒细菌容易传播,孩子抵抗力弱,可能会发生呼吸道感染。”今年北京的冬天是暖冬,几乎没下过雪,天气也不好。“甚至连春节期间,我们科的楼道里还加满了床位,医院里过年呐,这都是没办法。”实际上,孩子容易生病和环境的变化也有关联。“雾霾中潜伏的细菌病毒含量,比好天气时浓度要高得多。比如近期流行的病毒型甲流、轮状病毒、支原体肺炎还在持续。”在王琨蒂看来,雾霾对孩子呼吸道的伤害,往往最为明显和直接。“只要是一轮雾霾开始,每天上急诊来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就多起来。”医院儿科急诊的常态。自从年开始轮值儿科急诊以来,王琨蒂每天和抗生素打交道的频率就变得频繁起来。细菌感染是儿科常见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化脓性扁桃体炎,以及具有传染性的猩红热等。如果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果往往严重。“但很多家长对抗生素的第一反应却是抗拒:抗生素有副作用,这么点小孩能用吗?”实际上,儿科大夫必定是根据孩子的实际病情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绝不是信口开河。“如果是病毒感染,用了抗生素也无效,可如果是细菌感染,那该用就得用。”为了消除家长对抗生素的疑虑,王琨蒂在门诊时,常常手指着化验单,一项项跟家长解释为什么要用抗生素。可即便如此,也常常有家长始终心存疑虑。王琨蒂就遇到过一位特别纠结的父亲。夜里11点半,这位父亲带着孩子来看急诊,不到1岁的孩子软软地抱在手里。王琨蒂一问,原来是孩子腹泻了,大便里有点血。“大便验出来红白细胞都挺多,又不够痢疾标准。”王琨蒂判断,孩子得的是细菌感染的肠炎,得用抗生素。但这位父亲却忧心忡忡,反复一遍遍问着:“能不能不吃抗生素?不吃能不能好?要是不好的话,会不会加重?加重了会是什么表现?会有什么后果?……”王琨蒂其实很能理解这位父亲的矛盾心理——“他特别关心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早点好,但当要用到他认为可能引起副作用的药物时,他又不想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就想把这个选择题交给医生,可对医生的判断他又无法彻底放心。”王琨蒂解释得口干舌燥,一直磨到夜里12点多,诊室外都没人了,也没能消除这位纠结父亲的焦虑。除了像这位父亲般犹豫纠结的家长之外,直接拒绝使用抗生素的家长也并不少见。医院儿科大夫韩彤妍几乎每周门诊总能遇上一两位,直接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我们孩子不用抗生素。”“实际上,在医院儿科门诊开出来的抗生素,肯定是适用于儿童的。有时候家长的过度担心,其实是没必要的。”在韩彤妍看来,这背后的根源,医院和医生的信任缺失,以及对抗生素等药物不够了解。“儿科的特殊性恰恰在于病人本身没有多少决定力,几乎都是家长来代为做主。可家长的判断,有时候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擾,不一定听得进医生的话。”即便医生跟家长使劲解释了抗生素的治疗作用,副作用并没有想象中强,即便家长勉强同意把抗生素开回家了,也可能坚决不吃。“等到来复查时,总能想出各种借口推搪。”更有甚者,有家长固执地希望医生顺着他的思路和判断来,一旦你不赞成他,他就不信任你。来回劝说无效,双方的火都顶到嗓子眼了。这时候家长也烦了,愤愤丢下一句:“我挂专家号去,不跟你这普通号费劲。”留下韩彤妍在心里苦笑:“实际上,我也坐诊专家号。”可面对家长的抵触心理,她也常常无能为力。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极端是,家长死活要求給孩子输液挂水。“一进门就风风火火,说孩子病了得赶紧输液,我们孩子平时抵抗力差,每次得病都要挂水挂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但实际上,韩彤妍一检查,发现孩子得的是病毒型感染,用抗生素输液也丝毫不起作用。如何劝说,往往让韩彤妍煞费苦心。她常常跟家长说,要衡量孩子是不是有必要受这个罪?“打点滴对小孩子来说很费劲,动来动去针口一下子就鼓了,得重新扎,孩子哭得就更厉害了。家长也跟着受罪,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地两三个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有的家长犹犹豫豫地也就放弃输液了,但也有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非得坚持打点滴的固执家长。在儿科急诊和门诊里,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医生的工作也考验着人际沟通能力。“实际上百分之六七十的医疗纠纷,说到底都是沟通问题——医生说的话病人没听懂,或没有用病人能听懂的方式说出来。”在韩彤妍看来,家长心里本来就火烧火燎的,门诊时间又极为有限,医生就更得耐心。而王琨蒂在急诊室值班时,一年里要接诊将近两万病人,她始终认为:“你现在多说十句话把矛盾消除,则意味着你以后能少说一百句解释矛盾的话。”医生与家长的“折中”实际上用不用抗生素、用何种抗生素,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看来,首先应是一个医学判断。“什么是抗生素?”其实在医生和家长的理解语境里,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抗生素指的是抗生物病原体的制剂,而生物病原体就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等等。而老百姓嘴里常说的抗生素,是特指抗细菌的抗生素,这是应该明确的。”“常常有家长问我,这种抗生素是不是劲儿大一些?”实际上,抗生素并没有所谓强弱好坏之分,每种抗生素针对的抗菌谱不一样。“比如孩子在夏天里又吐又拉,大便里红白细胞都有,诊断为痢疾或肠道细菌感染,常用的是头孢三代。而孩子得了化脓性呼吸道感染类疾病,常用的则是头孢二代。便有家长不理解,是不是三代比二代杀菌力强?”实际上,区别只是二者对应的抗菌谱不同——肠道细菌往往以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较多,对应的抗生素是头孢三代;而化脓性呼吸道感染类疾病则以革兰氏阳性球菌较多,对应的抗生素是头孢二代。“抗生素的杀菌力并没有可比性。”在宋红梅看来,“选择针对感染的某一类细菌有效的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是大夫应该做的事,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宋红梅强调,病毒感染的情况没必要用抗生素,而细菌、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就一定要用。如若不用,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进而造成病情迁延和其他问题。“比如说链球菌感染,如果治疗不彻底,经常会合并风湿热,引起链球菌感染肾小球肾炎,这在过去是很常见的情形。”如今这种并发症少了,恰恰是得益于抗生素使用及时,治疗彻底。尽管用不用抗生素的判断权,看似应该牢牢握在医生手里,但现实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在幼儿病情的早期,鉴别是否是细菌感染有时候难度很大,有一定的复杂性。”王琨蒂告诉本刊,“儿童的各种感染性疾病早期都可能以发热作为主要表现,拿肺炎来说吧,不管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早期都可能出现发热、咳嗽、咳痰,这些症状的差异程度并不大。”尽管现代医学有相应的检验来辅助诊断,最常用是血常规和尿便常规和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指标。但儿科患儿在病原体方面会有一些特殊性,加之病史获得难度更大,临床症状也与成人有所区别——这所有的一切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诊断都能依靠实验室检验完成,还有一部分也是经验性判断。从王琨蒂的经验来看:“学龄前儿童最主要的疾病是上呼吸道感染,其中85%是病毒感染的自限性疾病,不需治疗,通过家长护理和饮食调整就可以痊愈。只有10%~15%是细菌感染引起,这些患者首先推荐口服抗生素,其次是肌肉注射,最后才使用静脉注射。”可既然是经验性判断,就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孩子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查出来的血相或许还很难立马决断,绝对是病毒还是细菌。”王琨蒂心里明白,“病情的发展有时候是很难预料的,加上门诊的随访复查无法做到很及时,坚持自己的判断有时反而会落家长的埋怨,为什么不早听他的马上输液?”当面对家长的催促、焦虑与指责,医生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妥协?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下定的决心。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在医生的判断和家长的态度之间寻求折中与妥协。至此,“用不用抗生素”折射出的已不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掺杂了社会环境、人心考量、医患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的权衡。而为了加强诊断的确定性,势必增加很多检查来辅助判断。“比如说孩子急性发烧,但其他情况都挺好,我就觉得先观察吧,不用非得立刻就做各种检查使劲去查。”可有的家长就特别纠结,基层医生为了慎重起见或顺着家长的意思,便开出各种检查单子。宋红梅却不主张过度检查:“孩子检查受到的痛苦,跟得到的检查结果之间,性价比太低。回家先观察,有情况了再查。”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这样的理念,医院之间做检查。“尤其是放射类的检查,不要随便给孩子做。如果医生听诊认为,肺里没有问题的可能性是80%,那为什么非要给孩子拍一个片子,让孩子吃一些射线呢?”用最小的药物副作用和检查风险伤害,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医院儿科追求的目标。宋红梅每周出大量门诊,但一年下来也开不了几个X光片检验单子。“如果说没有拍片子,你说我能保证%正确吗?也不一定。”在她看来,关键的问题或许是:作为医生你对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没有自信?对不确定的风险敢不敢承担?“说实话,我们做大夫,有时候真是胆战心惊。”即便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宋红梅在门诊时也很难做到时时笃定,“就像张孝骞教授所说的那样,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怎能不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夫在面对病人和病情时,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真的不是能%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希望家长和病人来共同理解。”抗生素里的效益风险比當病人无法理解治疗中存在的风险,不愿与医生共担风险时,医生也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这是当今国内医疗环境之下的无奈现状。“你不信任我,我就不敢给你治疗,我要治了以后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而医生束手束脚的后果,往往是更倾向于做出保守的治疗选择。“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病人如果做手术可能有50%的死亡率,如果不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就是%的死亡率——这种情况下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宋红梅说,“如果病人信任大夫,大夫就豁得出去,咱们共同面对共同承担风险,还有50%的希望。如果病人不信任大夫,大夫当然就不敢做了。”实际上,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也同样投射着类似的心态。“尤其对于慢性的疑难感染来说,真的需要病人和家属有很高的依从性。”宋红梅对一个案例印象很深。“这个孩子是中耳的慢性感染,进而造成周边骨质破坏,在山东老家治疗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好,医院。”一开始宋红梅考虑是否是肿瘤,但检查发现没有肿瘤迹象,便排除了。病理检查显示就是个慢性炎症,但按照炎症性疾病治疗,效果也不佳。一时之间,医生们不知从何入手。“最后经过细菌培养发现,可能是感染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致病菌。”但宋红梅和医生们也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病因。她便跟家长沟通,是不是按这个思路尝试治疗?“相应的抗生素疗程要长达三个多月,但家长依然愿意配合。”尽管在用药的最初两周不见效果时,家长也会有迟疑和担忧,但他依然愿意和医生们继续尝试,共担风险。果不其然,到了用药的第四周,孩子的症状就明显好转了。宋红梅很感怀家长的信任与配合,才有了医生们放手一搏的基础。“但有时候,要让家长信任和配合真是很困难的事。”有一位家长长期在宋红梅这里看病,但却特别不遵医嘱,让宋红梅感到头疼。“孩子是个普通感冒,我告诉家长不用吃抗生素,但家长总不听,总是自己去药店买来‘头孢先吃上,发现不管用了再跑来哭诉,怎么不管用?”这让宋红梅有些哭笑不得,“你这种情况不需要吃抗生素,当然不管用了。”“可等到孩子有一次真是扁桃腺化脓感染了,应该吃抗生素甚至输液时,原本应该输液5~7天的疗程,孩子输了两天不烧了,家长又擅自停掉输液。”实际上,孩子的体内仍然有细菌残留,并没有除尽。于是,很快孩子的病情又反复了。面对这种依从性极差的家长,宋红梅总有些恨铁不成钢:“不听医生的专业判断,家长擅自替孩子来决定停不停药,难道不觉得这是对孩子的极不负责吗?”而有时家长对药物副作用的恐惧,甚至到了让宋红梅无法理解的地步。她遇到过一个特别可惜的病例。“一个11岁的男孩得了红斑狼疮,必须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但男孩的妈妈就是不愿意,担心糖皮质激素副作用大。”实际上红斑狼疮在临床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5年生存率在90%以上没问题。“最后我都跟孩子妈妈说到什么程度,不用药这孩子就没命了呀!”但家长仍然偏执得可怕,甚至自动出院宁愿不治了。“孩子特别可怜,说妈妈不让他吃药。”宋红梅痛心疾首,“这不就是为孩子选择了一条死路吗?”“用不用药,不要只看到药的副作用,应该首先考虑药的正作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是不是得了必须要用这个药的病?如果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副作用,这是医生肯定要考虑的事。家长不能一来就说药的副作用大,坚决不能用。”在宋红梅看来,病人和家长应该正确理解药物的效益风险比——享受疗效的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不想承担任何风险也必然无法享受疗效。如同享受阳光的同时,就必然要承受阳光背面落下的阴影,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效益与风险的共担。但现实往往是,很多家长并没有跟医生共同面对、共担风险的意识。更让宋红梅感到纠结的是,某些超适应症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用抗生素?比如说喹诺酮类抗生素,考虑到它对儿童软骨发育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又结合我国的国情,说明书里明确限制儿科使用。“但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特别严重的耐药菌感染,只有喹诺酮抗生素有效,如果不用,孩子的感染可能就控制不住了,甚至可能因此丧命。”——这种情况下,是用抗生素还是不用?事实上,对于超适应症用药,我国法律没有给医生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任何空间。“只要用了就是违规,一旦出了问题医生就得担责任。即便征得了家长的同意和签字,也可能存在风险。”遇到这种情况,宋红梅往往特别纠结。“有的大夫可能会说,如果用了,就属于超说明书用药,万一出了问题打官司肯定会输,那我为什么非要用?可从救死扶伤的角度来看,即便孩子可能因为用药留下某些后遗症,但在用了药就能保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用?是不是也可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法律的空间?”抗生素用药理性对于儿科大夫来说,在抗生素使用的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是难以鉴别出是否为细菌感染,以及是何种细菌感染。临床上15%的细菌、真菌或支原体等感染一旦被确认,及时、合理地使用抗生素就不再是一个还要犹豫的问题。病程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千变万化,单靠孩子的免疫力去战胜细菌的侵扰显得过于势单力薄,抗生素的价值就在于缩短病程,用药就是为了保证它不往更坏的方向走。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则是一门极大的学问。儿童使用抗生素确实比成人要更加谨慎。孩子年龄越小,各个脏器的发育越不成熟,那么对药物的代谢、排泄缓慢,解毒能力越弱。因此不仅在用药范围,在用药剂量、用药间隔时间和总疗程上都有特殊要求。用药后相对大人更容易有副作用,因此要密切观察用药反应。“一些抗生素药物如氨基糖苷类(庆大霉素)和喹诺酮类(氧氟沙星)分别对听神经和儿童软骨发育有不良影响,在儿童使用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四环素类的抗生素对牙釉质发育有一些影响,过去我们有一些四环素牙,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大剂量应用四环素造成的,一般说来,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用四环素类抗生素的。”宋红梅说。多位儿科医生都反复强调,使用抗生素不仅要对症,也要保证足量和足够疗程。首先是细菌增殖的方式所限,抗生素使用需要一定的持续性。“细菌有一个增殖过程,有时抗生素发挥作用时,细菌还没有进入到增殖周期,此时抗生素对它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須持续用药,使得细菌在增殖高峰时能够被消灭掉。”王琨蒂说,“有些家长觉得今天不烧了,明天就不吃了,这个是不对的,这反而是在锻炼细菌的耐药能力呢!一定要在大夫的指导下用够量、用够疗程才行。”“小孩用抗生素的时候,用药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计算,而不能大人自行推测。”韩彤妍强调,幼儿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药量,儿童也要根据年龄和体重的不同来计算药量。“实际上对于年龄偏大的孩子来说用药量相对偏小,越小的小孩用药量越偏大,跟成人比也是这样的。”不同的药分别有复杂而特殊的使用剂量要求,儿科医生在开药时需要全神贯注,他们的脑子里正在进行一个严格的计算过程。“抗生素的一般给药方式是优先口服,能口服就不选择静脉注射。”韩彤妍说,“首先口服方便,尤其是大一些的孩子,能口服的剂型会很多。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因为不会吞咽,只能选择冲剂、分散片等有限的剂型。但如果只是普通的细菌感染,口服就足够了。静脉注射直接进入到血液中,能够让抗生素在体内迅速达到需要的血药浓度,效果一定是比口服要快,但静脉注射有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药都配备有皮试液,在打点滴时,家长、孩子和医生都承担很大的风险。“至于如何判断口服与输液的临界点,这是医生根据经验来做的个性化选择。”家长对抗生素的抗拒常常来自两种恐慌——耐药性和副作用。几位医生都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体耐药性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耐药菌株的产生,通常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而在体内产生了自己的耐药菌株。”在宋红梅看来,耐药性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抗生素广泛使用后,耐药菌越来越多,会在人际间传播,并不一定会在抗生素使用者身上发病。“所谓的耐药,实际上它是整体环境的耐药,在自然界里广泛存在的细菌是耐药的。你感染的菌是耐药菌,并不是说你机体就是耐药的。”抗生素的副作用也并没有想象中严重。孩子服用抗生素以后,经肾脏和肝脏代谢,只要不超过正常值,都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副作用。王琨蒂告诉本刊:“退一步说,如果吃药对身体有影响的话,绝大多数也都是一过性的,就是说你用药期间,可能会有反应,不用了,它就逐渐修复了。人的生命力其实非常强,你觉得小婴儿非常非常脆弱,但其实他们都是有很好的自我修复能力。”每个家长看到孩子生病,都有比对自己本身更加强烈的意愿,希望孩子能迅速好起来,医院,就会是一个很纠结的选项:不去,怕万一有什么闪失;去了,大夫即使为了安抚你,也会开些鸡肋的药物,吃不吃,心里都不舒服。其实在儿科大夫眼里,在孩子有些发烧和轻微上呼吸道感染的初期,家长完全可以通过在家里的精心看护渡过难关。如果发烧了,家长并不必单纯因为温度太高而紧张。“温度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先用退烧药再继续观察。”王琨蒂遇到烧了10分钟就来急诊的家长,来了做检查也没意义,因为血象反应没那么快。“每个孩子对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的致热反应不一样,有可能病毒感染导致高烧40摄氏度,但这孩子活蹦乱跳啥事都没有。也有脑炎患者体温只有38摄氏度的,因此不能单纯拿体温做依据。”在韩彤妍看来,“如果吃了退烧药体温降下来,孩子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或者只是一些轻微的咳嗽、流鼻涕的症状,不存在腹泻、呕吐等问题,一般都可以再继续观察——多喝水,吃清淡,三天还不见好再就诊也不迟。但如果是三个月龄以下的新生儿发烧就不能马虎,医院的。”而在宋红梅看来,家中只要常备退烧药就够了。“我经常跟家长说,发烧对孩子不一定是件坏事,像发烧、咳嗽,这都是我们机体保护性的生理反应,比方说发烧38摄氏度的时候,体内感染的细菌、病毒是不生长繁殖的,同时免疫力、细胞的吞噬功能又增强了。”她强调,“只不过别让发烧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实际上这跟抗生素的道理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怎么理性用好。”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ebsaw.com/jbjc/9661.html
